|
|
亲,以车会友,扩大圈子。注册一下吧?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免费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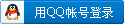

×
恐飞症患者的“武装”攻略(图)
每次收到出国邀请,我都会有一个漫长的心理斗争过程。一边是世界版图上又多插一面小红旗的诱惑,一边是对于长途飞行的巨大恐惧。
很多人都认为,飞机坐得太少,才会对坐飞机有恐惧,就像以前对于晕车的观点一样,“多坐坐就好了”。而我的恐机,我深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因——在入行不久的1999年,那年空难好像特多,年底了,报社总编交给我一个祸害我终生的任务——将全年的空难做一个大专题。那一周,我就是在一场血雨腥风中度过的。本来的小概率事件,在盘点整理中,其危险性和绝望感被无限放大,而我,也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。
对于空难发生概率之低,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。据说是如果有人每天坐一次飞机,要3223年才遇上一次空难。数据可以理性地说明问题,但是在现实世界,身边的一点小小的不寻常,都会让我的飞行过程充满坎坷和惊悚。
一次在从澳大利亚飞回上海的途中,或许洋面上的气流比较频发的缘故,这个飞行过程非常颠簸。我实在受不了了,就按铃叫来空姐。
“你们有镇静剂吗?”空姐第一次碰到这种怪乘客,问我:“你哪里不舒服吗?”“飞机颠得太厉害,我忍受不了了。”
空姐释然了,然后做出在过道跑步的姿势试图让我放松:“没事呀,你看,我还可以跑步呢。”
因为颠簸,她跑得踉踉跄跄的,我脸色苍白而绝望地说:“好吧……”<:TRS_PAGE_SEPARATOR>
每次飞行途中,身边人浑然不觉呼呼大睡的样子,真不知道有多让我羡慕。没有镇静剂,没人来把我一拳打晕,于是,我就只能自己制定一套减压的措施,方法如下:
首先,飞行的前几天晚上,电视上若有任何血腥的事故镜头,我一律不能看;去机场的路上,我必须不停地听MP3里的摇滚音乐,以武装一颗脆弱的心灵;在候机的时候,尽量不看那些苦命薄相的人,以免产生不良联想;一上飞机,戴好耳塞,努力让自己睡着,希望可以忽略起飞时的不适——当然,这招从来都没有成功过,因为飞行途中,我是一刻都无法入眠的;最后使出杀手锏,只要有酒水供应,我就绝对不客气地不断要红酒,至少酒精可以麻痹绷紧的神经。有一次飞机颠簸得实在厉害,我就一杯一杯地不停喝酒,幸亏那只是1个半小时的飞行,若飞得更长久些,我就要被抬下飞机了。
纵观身边人,有神经超级大条无视气流的人,甚至还有人遇到过氧气面罩脱落的紧急情况,即便如此,人家现在还淡定地飞来飞去。当然,也有比我更严重的绝对不坐飞机的。最近知道一位神人,国内一旅游杂志的主编,是个彻底的恐机症患者。据说他2001年“911”期间正好在洛杉矶,电视上看到了撞机的画面,世界瞬间崩塌——不过我好奇,他后来是怎么回的中国。
我同事中,也有一位是恐机症患者。我们的工作性质有很多出国机会,每次她都貌似战胜了自己说可以去,但是最终永远是临阵退缩;最近一次好像没有掉链子,准备材料、预约签证一切正常,结果对方因为行程问题取消了出国,她那天在办公室表现得兴奋异常,仿佛焕然新生一般——看来,“被放下包袱”也是一种幸福啊。而她最夸张的一次,是坐飞机去了澳门之后,终于崩溃了,于是辗转从澳门坐船到香港,再买火车票回上海。而由于没有买到当天的火车票,她又被迫在香港住了一晚,原本只要2个多小时的旅途,被生生拉长了很多倍——可是对于恐机症患者来说,浪费点时间和钞票算得了什么呢,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旅程,再长都不会让他们焦躁的。
比起她,我还处在灰暗地带属于可以被掰正的那类。一次出国,公关工作非常细致,出发前的问卷里,有“你有什么不适应的或者特殊要求?”一栏,我填写了“恐机”。我的意思是,尽量少安排短途飞行,能火车最好火车。对方紧张了,一个电话追过来问我恐到什么程度,因为这份问卷是要交给主办方老外看的,他们会对我这种情况很在意,搞不好就直接把我从邀请名单里勾掉了。
|
|
